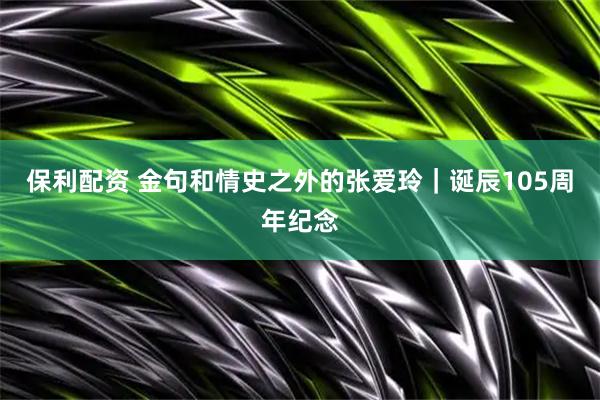
今天,是张爱玲诞辰105周年的纪念日。
“金句女王”张爱玲总是能用恰如其分的比喻写透人性,比如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蚤子”,再比如“红玫瑰与蚊子血”“白月光与饭粘子”。
这些金句,作为她作品的碎片,许多年后仍然被人们广泛引用。但她作品的全貌却常被“只言片语”的金句所遮蔽,她人生的真实况味也因情史八卦和身世传奇变得模糊。
若要真正理解张爱玲,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回到她的作品中去。她七岁开始写小说,十九岁成名,直到七十五岁在异国公寓悄然离世,张爱玲拥有近七十年的写作生涯。
她的一生,是一场漫长的漂泊与书写。从上海到香港,再远渡重洋赴美国,文学是她对抗时间、理解命运、安放自我的舟楫。
这张“叉腰照”,拍摄于1954年的香港,起初用于《纽约时报》书评版面,最终成为了张爱玲最为人熟知的视觉符号,仿佛她文学生命的浓缩——骄傲、独立、疏离、苍凉。
展开剩余90%01上海童年:旧梦华美的序章(1920-1939)
张爱玲的生命底色,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末世的悲凉。
1920年9月30日,她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栋没落贵族府邸。她的曾外祖父是李鸿章,祖父是张佩纶,两人都是晚清名臣;但到她父亲这一代,家道早已中落。她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,抽鸦片、娶姨太,沉湎于旧时代的幻梦;母亲则受新式教育影响,两度赴欧留学,最终选择离家出走。
一边是腐朽的古典传统,一边是西式文明的冲击,这个分裂的家庭是张爱玲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,也成了她日后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
两、三岁时的张爱玲
人们常说,“诗穷而后工”,伟大的作品是对苦难的超越。张爱玲亦是如此。父母的常年不和、家庭的动荡不安,让她过早地体会到人生的荒谬与人性的复杂。
她在散文《天才梦》中写道: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蚤子。”这句天才式的断言,几乎预示了她未来所有作品的基调——在华丽的表象之下,是千疮百孔的真实。
在苦闷的青少年时期,张爱玲把自己埋进书本,借以逃脱现实生活的不堪。她读《红楼梦》、读狄更斯、读毛姆,也试着写悲情小说,给英文报纸投影评。
她不曾享受美好的青春,却在这个过程中默默积蓄着能量,为日后那一部部惊人之作,悄悄地做好了准备。
02沪港双城:传奇的诞生与顶峰(1939-1944)
1939年,张爱玲背井离乡,入读香港大学。在港大文学院,张爱玲主修英文与历史,辅修中文及翻译。
彼时港大的学生背景多元,有何东爵士的侄女侄子,有橡胶大王、万金油大王的子女,还有汪精卫的侄女,大多家境优渥。而张爱玲靠着单亲母亲艰难的供养,经济十分拮据,是港大唯一没有自来水笔的学生。
深知母亲的不易,张爱玲学习极为刻苦,成绩近乎完美。她日夜苦读英文,对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烂熟于心,三年间给母亲和姑姑的信件,皆用英文书写。
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成绩单
1941年12月8日,太平洋战争爆发,港战随之打响,香港大学被迫停课。
原本沉浸于英文读物的她,在战火纷飞中,一头扎进冯平山图书馆馆藏的明清旧小说里。在《烬余录》(后收录于《流言》)中她曾写道:“在炮火下我看完了《官场现形记》。” 当时的环境危险,字印得极小,光线也不充足,但她想着 “一个炸弹下来,还要眼睛做什么呢?——‘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’”
1942年5月,香港完全沦陷后,张爱玲乘船返回上海,暂居在姑姑张茂渊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。
此时的上海,已沦陷近5年,孤岛时期的文化繁荣不再,巴金、茅盾、张恨水等知名作家的名字,已从沪上文艺报刊消失,文化界出现大片空白,这恰好为张爱玲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。
她偏爱中国古代白话,行文效仿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。她带着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和《沉香屑·第二炉香》的手稿,登门拜访《紫罗兰》杂志主编周瘦鹃。张爱玲的文风很对周的胃口,很快,这两篇小说在《紫罗兰》上发表,两炉香灰燃起了整个上海滩对她的文字的热情。
此后,张爱玲的多篇小说和散文在《杂志》《万象》等刊物发表,她的第一部小说集《传奇》初版发行仅四天,便销售一空,张爱玲就此成为沪上最炙手可热的作家。
《传奇》中收录了《金锁记》《倾城之恋》《封锁》等十篇小说。在《倾城之恋》中,她借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俗世姻缘,展现出历史洪流对个人命运偶然又讽刺的重塑;《金锁记》则以曹七巧的一生为主线,写尽一个女子如何被金钱与情欲扭曲成复仇的幽灵;同样精妙的还有《封锁》,一辆暂停的电车让短暂的精神之恋得以发生又迅速幻灭,成为她整个文学世界的隐喻。
正是在这一时期,张爱玲以早熟的才情、华丽的文风与尖锐的洞察,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文学王国。她不止在写爱情,更在写人的卑微与伟大、虚伪与真实,写乱世之下个体如何挣扎、如何妥协,又如何存活。
03时代转折:漂泊的开端(1944-1955)
战争结束后,上海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变,张爱玲个人生活与创作也步入了全新阶段。
1944年,张爱玲结识了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。
两人初次见面,胡兰成便被张爱玲独特的气质与才情所吸引,随后他频繁拜访张爱玲,在一来一往的交谈中,张爱玲也对这个思想敏锐、能言善道的男人动了心。
尽管胡兰成已有家室,且政治立场饱受争议,但爱情的热烈让张爱玲选择奋不顾身,二人很快陷入热恋,并于当年秘密成婚。
然而,好景不长,胡兰成婚后不久便与他人暧昧不清,甚至在逃亡期间,也未停止与其他女子的纠缠。
这段感情给张爱玲带来了巨大的伤害,在给胡兰成的诀别信中,她写道“我已经不喜欢你了,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。......你不要来寻我,即或写信来,我亦是不看的了。”
胡兰成
在与胡兰成感情纠葛的这段时间,张爱玲的创作未曾停歇。她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(后改写为《半生缘》)与《小艾》(后收录于《怨女》)。相较于早期作品的锋芒毕露,这两部作品的风格明显趋于平实、醇厚。
《十八春》以沈世钧、顾曼桢为主角,讲述了两人相识、相恋,却因家庭、社会等种种因素,在命运的捉弄下错过彼此,最终各自离散的爱情悲剧。那句经典的“我们回不去了”,道尽人事变迁与命运无常;《小艾》则围绕丫鬟小艾展开,描绘了她在传统家庭的压迫下,历经苦难却顽强抗争的一生。
此时的张爱玲,少了些早期对华丽辞藻的雕琢,而是将更多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中,以细腻平实的文字,勾勒出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下的挣扎与无奈。
1952年,张爱玲再次离开上海前往香港。她先后在香港大学翻译中心、美国新闻处任职,从事翻译工作。期间,她开始创作未完成的遗作《异乡记》,书中记录了她从上海辗转他乡旅途中的见闻、孤寂与惶惑。
从此,上海成为她笔下一个永远无法触及、只能在记忆中反复回味的文学原乡。
04远赴美国:洗尽铅华的后半生(1955-1995)
长久以来,人们对张爱玲的美国岁月充满了“晚景凄凉”的想象。事实上,她从未停止写作。只是她的写作方式,从面向公众转向了更深邃的内向探索。
1956年,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美国剧作家赖雅结婚,婚后的生活并不顺遂,他们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顿,赖雅还饱受病痛折磨。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,张爱玲依然笔耕不辍,进行着英文小说创作与翻译。
这个时期,她最重要的工作之一,是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在《红楼梦魇》里,张爱玲逐字逐句比对不同版本的《红楼梦》,从细微处挖掘作者的原意、人物的命运走向,以及作品背后的时代密码。这一研究过程,既是她对文学经典的致敬,也是一种精神上的“还乡”。
1967年,赖雅在张爱玲的陪伴下离世。此后近三十年,她一直独居。张爱玲晚年的写作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她的语言变得愈发洗练、简约,甚至带有某种粗粝感。她的目光,也聚焦于自身的家族与记忆。
《小团圆》这部倾注了她半生心血的自传体小说,便是她对自己一生经历,尤其是与母亲和胡兰成关系的一次最彻底的梳理。书中,她采用了大量闪回式叙事,将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、挣扎、渴望与失望一一呈现。
《对照记》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,这是一本图文集。
从祖辈的显赫荣光,到父辈的落寞,再到自己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泊,每一张照片都饱含着她对家族历史的缅怀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。
通过《对照记》,张爱玲试图在众说纷纭中,夺回对自己形象的最终解释权,为自己的一生做最后的注脚。
1995年9月8日,房东发现她安详地躺在公寓的地毯上,盖着一条薄毯,仿佛只是小憩。法医判定,她已离世约一周时间。那个曾经说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蚤子”的人,以最安静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结语
从上海租界的早慧少女,到洛杉矶公寓的独居老人;从惊艳文坛的天才作家,到被无数文艺青年奉为偶像的文化符号,张爱玲的一生是一条不断远离故土的轨迹。然而,在文学的世界里,她从未离开。
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《细读张爱玲》一书中写道,“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作家,一句话就行了。一句话,你就会觉得和另一个时代、另一个空间的某人,心是相通的。而相比之下,挤在你身边周围、地铁上、公司里的那些人,他们挤在你的身边,其实离你很远。”
彩蛋
搜狐文化编辑部利用AI技术“复活”了张爱玲,请跟随我们穿越回百年前的老上海,和张爱玲一起City Walk。
撰文 | 张鹤妍
编辑 | 钱琪瑶
AI设计 | 周雨姗
发布于:北京市股票在线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